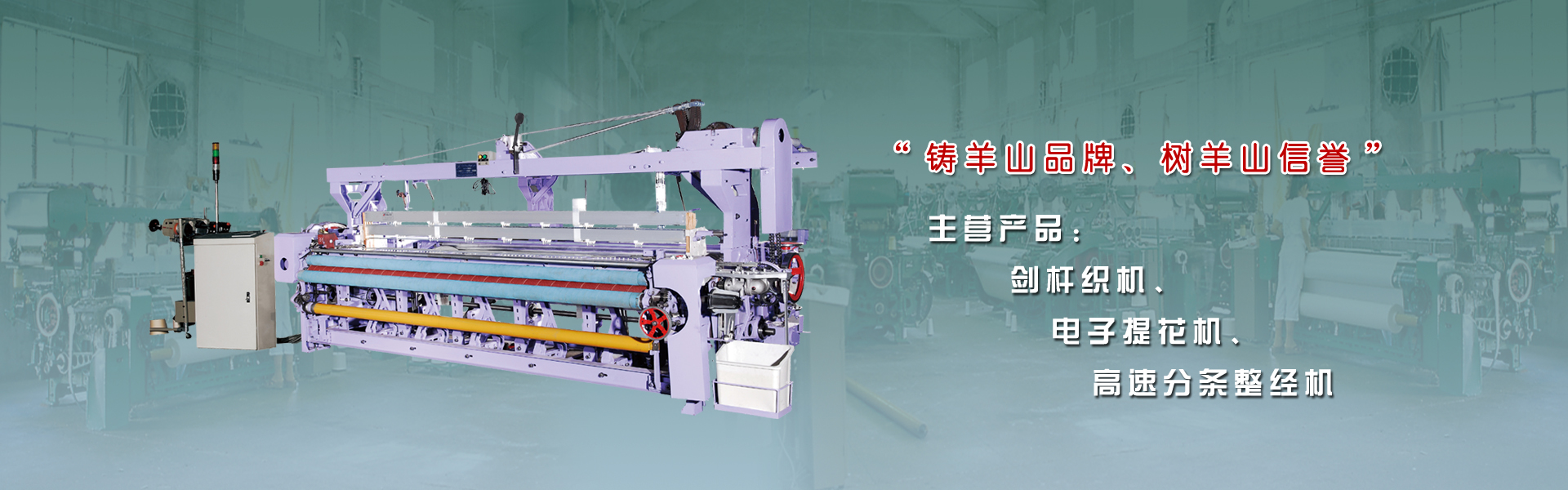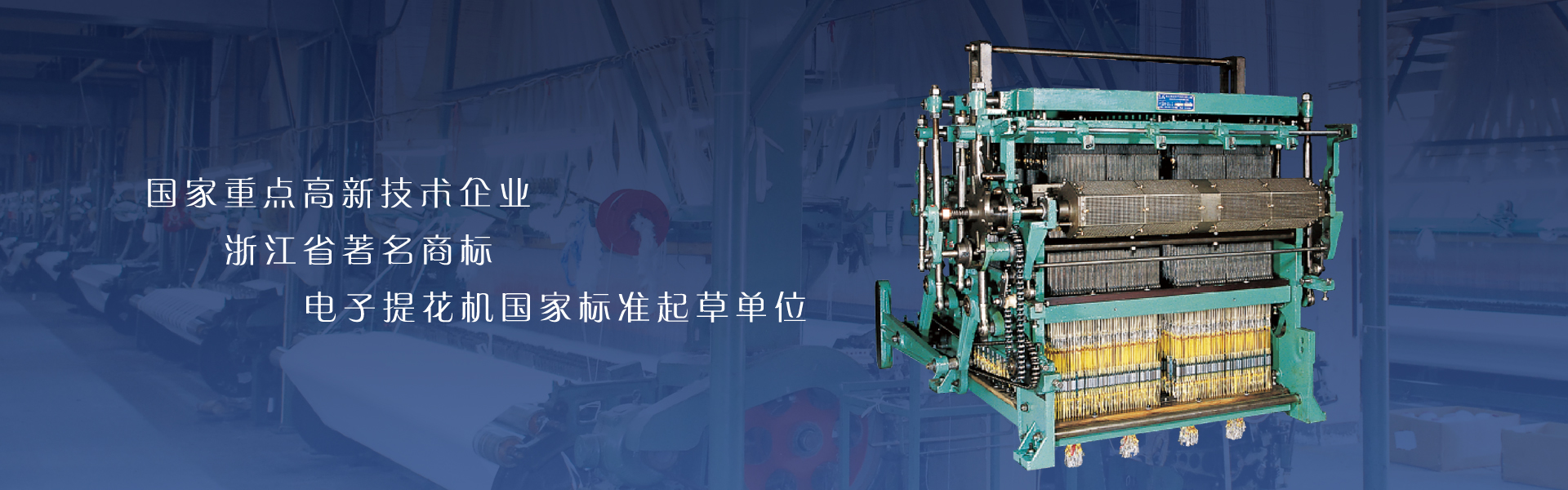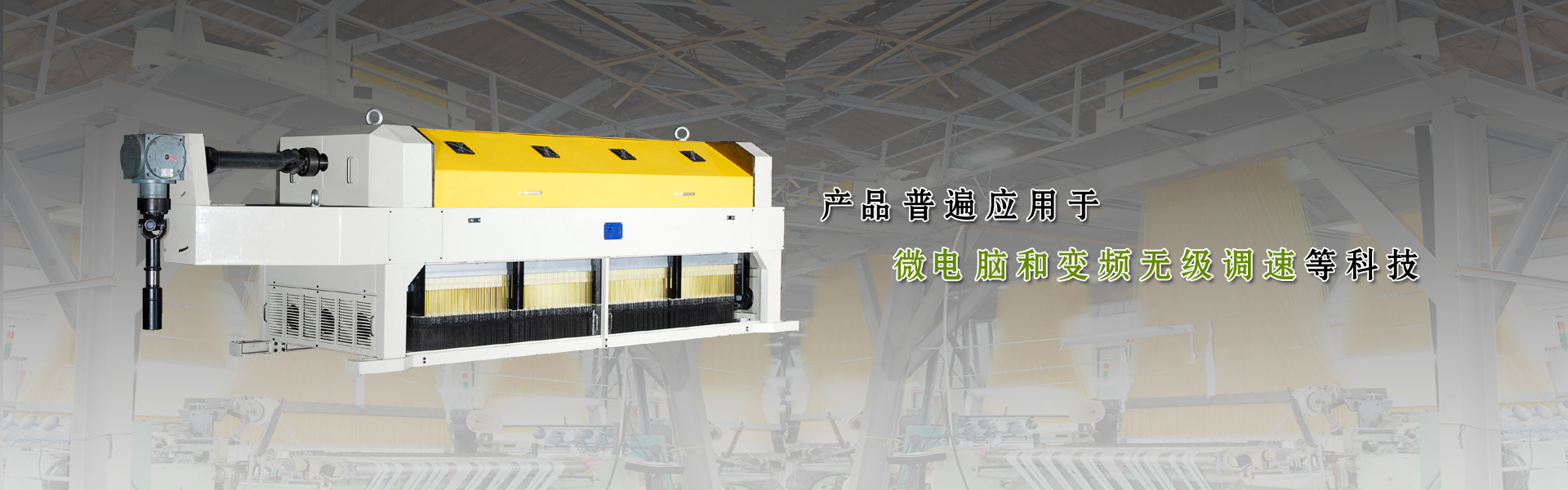普兰县-放在印度脑门上的利剑
于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孔雀河蜿蜒延绵,河流所经之处的河谷地带,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绿洲,中印“三大争议地区”之一的阿里普兰县就座落于此。
普兰县地处西南部,阿里南部地区,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之处,是阿里地区著名的边境县城之一。议其气候,享受着来自越过喜马拉雅山的孟加拉湾湿润海洋季风,普兰是阿里“最宜居地带”;谈其风景,圣湖、神山、庙宇增添她迷人的气质。
然而,时至今日,普兰县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其显要的军事地缘意义和国际贸易地位。

如果说西藏是“世界的屋脊”,那么普兰就是“世界屋脊的屋脊”。普兰县县内平均海拔超4500米,作为一个半农半牧县,该县的农民和牧民皆为藏族,同时,依山傍湖,风光明丽,历史悠远长久,旅游业和商贸服务业也是普兰县的重要经济收入之一。
普兰县坐落于阿碧峰和纳木那尼雪峰之间,该地放眼望去,满目皆是贫瘠而粗粝的荒滩、岩石,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里人烟稀少,1317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总数仅为1万出头,人口密度即0.93人每平方公里。雪山甚至比人还多——无论你在哪里,一抬首、一睁眼,就能清楚看到巍峨而圣洁的雪山。

雪山甚至比人还多——无论你在哪里,一抬首、一睁眼,就能清楚看到巍峨而圣洁的雪山。
普兰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随时代、通讯的发展,逐渐为人所知:圣湖玛旁雍措、鬼湖拉昂措、神山冈仁波齐、纳木那尼雪峰、象泉河、孔雀河等。
自古以来,玛旁雍措和冈仁波齐被印度佛教、西藏原生宗教苯教、藏传佛教、古耆那教等诸多教派的信徒奉为至高无上的“万水之源”和“千山之王”。
冈仁波齐象征着“仁慈和纯洁”,朝圣者称其为“阿里之巅”——尽管他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但却并非该地最高峰。

冈仁波齐的海波只有6656米,但他因金字塔式的峰形和山体,其峰顶横向岩层的自然构成和垂直而下的巨大冰槽同代表佛教力量的“万字符”十分相像,这为其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在普兰及世界各地的信徒眼中:冈仁波齐在哪里,神就在哪里。
2002年,从普兰口岸入境的外国人士超过65万人次,尽管当地人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圣湖神山,敬畏自然的每一寸土地,但地处三国交界地带,普兰县的文化旅游产业依旧越发兴盛。
除却名声大震的神山圣湖,普兰这个边境小城还保有洛桑王子及其2500多个“妃穴”,古商道、古宫九层引起拉姆飞升处、印度苦行僧、普兰彩石、普兰歌舞等等独具风韵的宝贵旅游资源。

神山和圣湖周边的各类自然资源被绝对禁止采用,其草木不得用作燃料,无论多么珍稀、昂贵的矿产也不得开采,动物也不允许捕猎。
如果需要开采其他区域的地下资源,需要做满一整套“征请”仪式,以示对神灵的尊重;同理,如果在开采过程中造成土壤中生命体的伤亡,事后也需要补充各种仪式,表达对神灵的歉意。
千百年一直如此,我国各大藏族聚居区的朝圣者和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信徒常常跋涉千里,他们从家乡,到阿里,从普兰县至高山之下的巴嘎那不到100公里的道路上,常常能够见到老幼相携的异国信徒。
1954年至1961年,普兰县来自印度的朝圣香客多大15000人次,1954年为藏历马年,“羊年转湖、马年转山”,当年的入境朝圣者更是多达1万余人。

自从对印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印之间就相继关停了各个通关口岸,原本直行的朝圣者不得不绕道尼泊尔,在行至边境的通关口岸,一同前往朝圣。他们其中不少人,为了朝圣变卖家业,素未谋面,却都微笑着以“拉马斯德”亲切问候。
2014年,为顺应国内呼声高涨的朝圣请愿,印度主动联系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开放一口岸,专以便利来自印度的虔诚的朝圣者。本着对信众的尊敬和善意,中方同意开放普兰县强拉山口口岸。
彼时,普兰边防检查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担负印度官方朝圣者出入境检查任务的边检机关,2014年6月20日,第一批印度的官方香客来到普兰县,这批香客来自印度的宗教界、国家机关和商界重要部门。

普兰公安出入境管理大队会主动背负沉重的行李、为年迈的老人检查身体、为不适的香客输送氧气、搀扶年老体弱者,普兰同印度有着五十多公里的中印边界线,一时间,中印关系之间因为纯洁而热烈的信徒之谊迎来了一段“回温期”。
2017年,狮泉河海关普兰工作点于强拉山口监管出入境印度官方香客1826人次,全年监管验放18批次印度香客,同比增长29%。同时,普兰县因地处中、印、尼三国交界处,区位优势显著,其边境贸易发展的潜在能力巨大。

如印度和尼泊尔具有重楼、小叶紫檀等名贵木材和药材,其进口木料价格在200元-400元/公斤,如果加工成为最简单的工艺品——手链,其在国内市场售价可达1000元——3000元/串,如是加工成为佛像、庙宇等高端工艺品,将得到更高的利润。
现如今,正对普兰县交通网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发育不成熟等等制约因素,开发部门正角力抓住区域协调这一关键,重塑当地民众“等要靠”的落后思想,慢慢地加强当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自主创业精神。

然而,中印边境之间的崎岖蜿蜒的隔阂依旧难以完全磨解,边界问题是横亘在中印两国关系纵深发展的“卡喉刺”,于宗教,普兰是一个神圣的和谐之地,然而,于军事地缘,普兰却不时亮出一丝硝烟的獠牙。
普兰县城往西南可以抵达中印边境,往南可以到达中尼边境,往北可以通向阿里噶尔县城,然而,通往阿里噶尔县城足足有398公里,通往中尼边境却只需10公里,对于普兰县人民而言,出一趟国,比去一次县城还要近。也正是因此,该地属于最接近边境冲突的地带。

2017年6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印度边防部队在中方于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之时,恶意越线阻拦。然而,中印边界线锡金段早已白纸黑字划定,印度独立后,其官方政府也多次以书面形式表示双方对锡金段的走向没有异议。
印度军队在此以背景之下,干涉中方在自己领土上的主权行为,纯属危害边疆地区安宁与和平。
2017年6月26日,正当中印边界关系紧张之际,印度反手向中国商品施压,宣布对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从中国进口的聚酯高强力纱线进行反倾销调查。就已经敲定的锡金段作此文章?必须得说,印度此举将其对阿里普兰县及其周遭地区的企图、身为南亚大国的气量暴露无遗。
可事实上,自从2014年,为满足印度朝圣者的强烈请求,中印商定开通乃堆拉山口朝圣路线以来,印度就开始了“蹬鼻子上脸”的顺竿操作,仿佛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在中印边界线年之后,印度在边界地区的道路、桥梁和建筑设施等基建快速的提升,甚至有巡逻官兵和边民反应,这些印度军队白天不修路,晚上偷偷修,一天就能修上一两公里。

印度军队会因为2017年的洞朗对峙而收敛在边境搞基建的动作吗?答案很显然,并不会。表面上看,印度的野心、企图被公之于国际社会,难看吃相暴露无遗,但以更为冷峻客观的目光看待此事,不难发现,印度军队仍就叼走了不少好处。
毋庸置疑,印军试探了中国的底线。他们通过洞朗对峙,明白中国不愿意落大国风度,他们预判,中国人不愿——或者说不敢交火,更倾向于和平解决。这一嚣张的做派很符合莫迪政府在中印边界推进的“攻势防御”和“前进政策”。
2020年,在中印建交70周年之际,印度贼心不死,在供印度香客朝圣进出的强拉山口边境地区修建了一些所谓的“建筑设施”,同时,还有一条长约80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足以将强拉山口于通往冈仁波齐的道路勾连起来。

当中国对印度这一行径予以警告之时,印度官方却宣称,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改善中印边境地区的通达性,以减轻朝圣者长途跋涉的辛劳,至于“建筑设施”,绝不是为军事筑设,只是为朝圣者准备的,一则为其提供遮风避雨之所,二则为其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医疗帮助”。
2020年5月初,中印双方就边境修筑公路和建筑设施的问题开始对峙,莫迪政府和着稀泥,头一次好声好气“劝”中国,和平解决此事,此时,印度军方满以为局势尽在掌握中,打算对中国领土由实地蚕食,进军至书面蚕食。
2020年6月,面对中国非同以往的强硬姿态,印军表现出了无赖的困惑:中国应当是不敢强硬的啊?

面对中国的铁腕抬掌,6月15日,在中印边境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印度军队故意越线发动挑衅,局势一目了然,因为印军吃了亏,其意识到中国要动真格了,所以慌乱闹事,企图搅乱中对印的逼退进程。
2020年8月29日印军再度非法越线,闯入中印边境西段地区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班公湖湖形狭长,在历史上,在湖泊原本全湖在中国境内,现如今,因为印度的蚕食,西侧地区约30%的面积位于印度实际控制区内。

河谷周边的狭长地带可以修筑公路,在物资贫瘠匮乏的高原山地地区,公路交通就是生命线。若论挑衅地点的挑选,班公湖沿岸无疑是印度的不二之择。
班公湖南岸设有一个DBO机场,该机场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存在,在大雪封山的时节可以为印军的物资运输机提供起降平台,保障印军对弹药、兵员和补给品的需求。
面对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的正常交涉,印度军队却对出面交涉的巡逻人员鸣枪威胁,事后还反咬一口,称是中国军队先开枪挑衅的。

正当中国国内义愤填膺之时,印度防长辛格明晃晃放话:“为了应对中国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基础设施的现状,印度将加大在中印边界重要道路和桥梁的基建预算。”
将目光放向控制班公湖南岸地区的印军,印方军队不再气急败坏,进击闹事了,前一阵疯疯嚷嚷的军队顿时变得有理有据,要求同中方和平协商解决此事。控制了易守难攻的战略制高点,便慢条斯理要求谈判,到底是和平谈判?还是乘机勒索?此一自是不言而喻。

为何印度在国际上口口声声以宗教道德绑架中国之时,中国依旧冷眼相抵?过去,印军在中印边境前线一直采取“蚕食政策”,其以胡搅蛮缠、扭曲事实的手脚,几乎占据了中印边界绝大部分的战略制高点。
原本在阿里噶尔县扎西岗乡的典角村——普兰县的邻县,有一个温泉,边民及其牲畜若是身上有不痛快之处,赶忙去温泉泡一泡,可谓是“神清气爽,百病全消”,然而现今这一温泉完全被印度军方所控制住了。

同时,在普兰、噶尔一带的边境地区,年轻边民的反蚕食意识和动力远远不及五六十岁的老年人,他们更为圆滑,也更为退怯。这是为何?
从中印边界调研而归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如是感慨:“因为我们没及时反制,久而久之,自然受制于人。”
如何反制,如何转劣势为优势呢?将目光放向印军虎视眈眈的普兰县,求一个答案。
由地图可见,普兰县距离印度河平原仅仅200公里,距离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也不过比前往县城噶尔多上36公里,同时,普兰同印度北阿坎德邦相邻,
由于普兰县内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普兰县之于印度,实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

2021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新建定日、隆子、普兰3个机场的工程建设项目,截至2017年底,普兰县户籍人口总数为9258人,非流动人口总数9657人,不足一万人,却要建造一个机场,很显然,这是明摆的“亏本生意”。
然而,生意会亏本,国防大业却不会陨落。包括普兰机场在内的三个机场,在平日里,既可以民用,于战时,也可以军用,支持军队作战,将对西南边陲的国防事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战斗机一个俯冲就能到达新德里”似乎不仅停留在说笑层面。
一直有着地势焦虑和“被害妄想症”的印度反应更为激烈,一旦中国能够顺利通过北阿坎德邦,便能一路高歌,推进至印度北方邦,甚至是中央邦等军事、政治中心。

尽管印度在北阿坎德邦的边境委派了重军把守,时刻检测普兰动向,尽管阿里普兰机场尚未完工,中国从未放弃通过外交和军事对话推进边界问题的和缓解决,依旧不影响印度国内媒体大肆炒作“”、“普兰”及“北阿坎德邦危机说”。
然而,在印方炒作普兰县之于北阿坎德邦的“绝对制裁作用”之时,事实却是,印度从未有一分一秒放弃蚕食属于中国的普兰县,将所谓的“军事威胁”正当化,将蚕食行为合理化。
可在印度渲染的“中国普兰威胁”背后,中国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未能真正拿起这把锋利的亮剑。因普兰县为中国领土,故中国秉持着卫疆御敌的心态,若说“人善被人欺”,之于当今中国军事实力显然托大,但正是因为中国雍然的姿态,给了印度可乘之机。
普兰的确存在一定的军事战略价值,但在现阶段的中印关系中,普兰县从被拿捏到反制印度,还需要很长一段路,从三大机场的修建开始,中方已然掌握绝大部分主动权,中印双方开始步入对峙和僵持阶段。

然而,2021年,伴随着普兰机场的的获批,还未等来中印边境因基建问题再生事端,却遭逢印度新冠疫情的疯狂失控。遑论印度军队,就连前来朝圣的印度香客、尼泊尔商人都被拒之境外。
中国军队协同普兰县党委一同死守边境管控,真正在普兰县内做到了边境线全面封堵,社会全面管控。中国戍边部队的压力是巨大的:于道义上,立足新冠肺炎大背景下,中国全面封禁普兰口岸及边境无可厚非,但这并不代表印度愿意配合“国际道义。

相反,中方戍边部队需要承担双重压力:国防安全和防疫安全。在新冠肺炎爆发的20多个月里,中印军队已经进行了长达20个月的边界对峙,终于,这一令人疲惫不堪的僵局在2022年新年的第一天得到了些微缓和。
2022年1月1日,中国军队和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上,包括“拉达克”地区东部的中印“摩擦点”在内的10个地点上,双方互相赠送新年糖果,互致新年问候。这一积极信号也为印度媒体所关注,并予以正面报道。

报道图中,中印双方军队代表全副武装,穿戴防护服和口罩,相隔一条浅浅的河流,不远不近地对望。这是中印两国一以贯之的传统,当日,印度军队也在中巴边境同巴基斯坦军队停火,双方进行了互赠糖果的仪式。
现如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印边界局势总体相对平稳,双方正在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推动中印边界保持对话畅通。

标题来源:《印度自以为把准了中国的脉,所以敢于咄咄逼人》;《观察者网》;2020-09-21
《印军为何十分看重班公湖南岸的这个地点?有它没它对印军区别很大》;《环球时报》;2020-09-02